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梁鸿、石一枫
来源:十月文学院(微信公众号) | 2018年08月13日09:10

编者按
6月20日上午,“十月作家居住地・丽江古城”第二场名家讲堂在丽江古城雪山书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十月文学院、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位入住“十月作家居住地・丽江古城”的作家梁鸿,和著名作家、《当代》杂志主编助理石一枫,围绕着“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展开了别有生趣又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对谈。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约,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和堂出席了本次活动,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丽江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丽江市文学界专家学者和丽江市作家协会成员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梁鸿和石一枫为大家梳理了传统观念中对乡土文化的两种封闭式的想象类型,呼吁大家对固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写作拥有塑造民族精神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梁鸿指出,乡村生活本质上是人的生活,有流动的需求和渴望,因此不管是愚昧落后亦或田园牧歌式的想象,都忽略了乡村流动性和开放性,应该用城乡相互生成的概念来代替传统二元对立的想象。石一枫认为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偶发和爆炸性的现象,人们应该打破城市改造乡村的文化等级秩序,他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谈到了人们对土地内在的依恋和回归情节,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需要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和美学规范。
城与乡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互相生成
梁鸿:我一直对丽江充满向往,这两天去了白沙古镇、束河古镇,也有了一些想法。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最大的主题就是改造乡村。不管是文化改造、经济改造还是农民进城,都能延伸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精神状态的问题,实际上当代作家是非常关注这个层面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潮之中,也需要考虑怎样去适应,去看待,或者思考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从现代以来,乡土中国经历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关于乡土的想象。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想象可能是,认为乡村是古老的、封闭的、一潭死水的,跟我们现代生活是完全分离的。还有一种关于乡土的想象是桃花源式的,大家都知道陶渊明,田园诗,从中感到乡土是非常非常美的。
关于乡土的想象,一直朝这两个维度发展,一方面觉得乡土是封闭的、固守的,我们需要去改造它,需要让它跟现代生活接轨,另外一种觉得乡土是田园诗一样的,它需要我们去维护、去坚守,不要变动它,或者它成为每个人心中一个古老的梦。但是就我的理解而言,我觉得这两种想象都是非常狭窄的或者片面的,都是把乡土世界、乡土文化、乡土的精神内涵做了一个固定的、悬于我们生活之上的思考。
其实在我的观察和思索里,乡土社会从来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乡土社会里面的农民、乡绅、普通生活的人,都是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即使中国最古老的乡村,保持着中国社会最古老的组织形态,它仍然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因为有人,所以都有向外流动的冲动和渴望。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并非是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以后,大家才知道出门打工挣钱,其实农民一直有这个愿望。
我们的当代文化、政治发展方向,把城乡二元对立变得非常固化。我曾经查过国务院1950-1959年关于农民的一个政策,阻止农民盲目进城。这群农民简称盲流。实际上,在一年年反复的阻止过程中,我们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二元对立的概念隔离开了,所以才有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这些观念的生成。我们看到很多文学写作里面,写到农民是多么保守,多么愚昧,在城市里面多么不适应,其实并非是天然的,这里面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原因和精神原因。
为什么在丽江刚好说这个话题?丽江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作为外地人,首先我们觉得丽江自然风景非常诱人,它的阳光、它的雪山、它的整体氛围这样美好。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丽江可能给大家塑造了一个梦,这个梦里面有两点:一个梦是所谓的田园诗,你来到这个地方,像桃花源一样非常美,你可以慢生活,你可以寻找那种悠远的关于古老生活形态的梦想。还有一个是所谓的逃离,城市人要逃离城市的繁忙,来到这个地方。这两种想象,也是延续了关于乡土的比较单一的、封闭的想象,这样一来,丽江是非常被动的,我们把丽江作为一个被动的田园风光形态的存在,而忽略了丽江人民或者丽江本地生活形态的开放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这展现了我们社会一种偏执的观念,我们把乡土作为一个固定、封闭的东西去处理它、去思考它,这是非常大的问题。石一枫刚好写过一些关于农民进城的作品,比如《世上已无陈金芳》,一直思考关于农民,关于乡土社会跟城市之间的冲突,关于乡土的生成的问题。我特别喜欢用“乡土生成”取代“城乡二元对立”这个词,因为“二元对立”是排斥性的,“乡土生成”是生长性的,是彼此在塑造的。
我当年写《出梁庄记》,因为要做调查,跑了好多城市,我发现实际上农民的形态,完全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塑造、生成出来的,并非天然就是愚昧、麻木的。据我的理解而言,乡村里面必然承载着一个人最古老的梦想,因为跟大地相关的东西总是很让人向往,但另一方面,这个大地也是行进在时代中的大地,它不是跟时代无关的大地,这才是比较开放的观点。
石一枫:我从小到大一直住在北京,也没出过北京,要说真正的乡村是什么样,我并没有看过。但后来想想,我的生活里面,乡村的因素也很多。中国的城市很特殊,发展的速度奇快无比。我们回想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比如丽江市,可能还叫丽江地区,想到昆明,再想到北京,其实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城市。
我从小到大住的地方,在今天北京叫西四环路。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老师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是郊区。北京的四环路,三十年前全是农田,今天想起来是很沧海桑田的。北京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你今天看到高楼大厦、很现代化的地方,它的名字都土的要命。比如中关村,为什么叫“村”?三十年前,它就是一个农田,就是一个村,有人在那里种地。比如太阳宫,今天是一个高级住宅区,挨着望京,10万块钱一平米,但是当年的太阳宫就是农田。
从我这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来,第一,我们的城市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偶发的、特殊的现象,是爆炸式出现的。前二十年,目睹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炸弹,在我们国家版图上炸开,把乡村全都炸成城市,炸成高楼大厦,炸成机场、高铁站,我们现在依然目睹这样的爆炸继续进行。武汉也在爆炸,郑州也在爆炸,合肥也在爆炸,今天所有炒房团炒到哪里,哪里就是爆炸最热闹的地方。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偶发的、突然的,甚至仓促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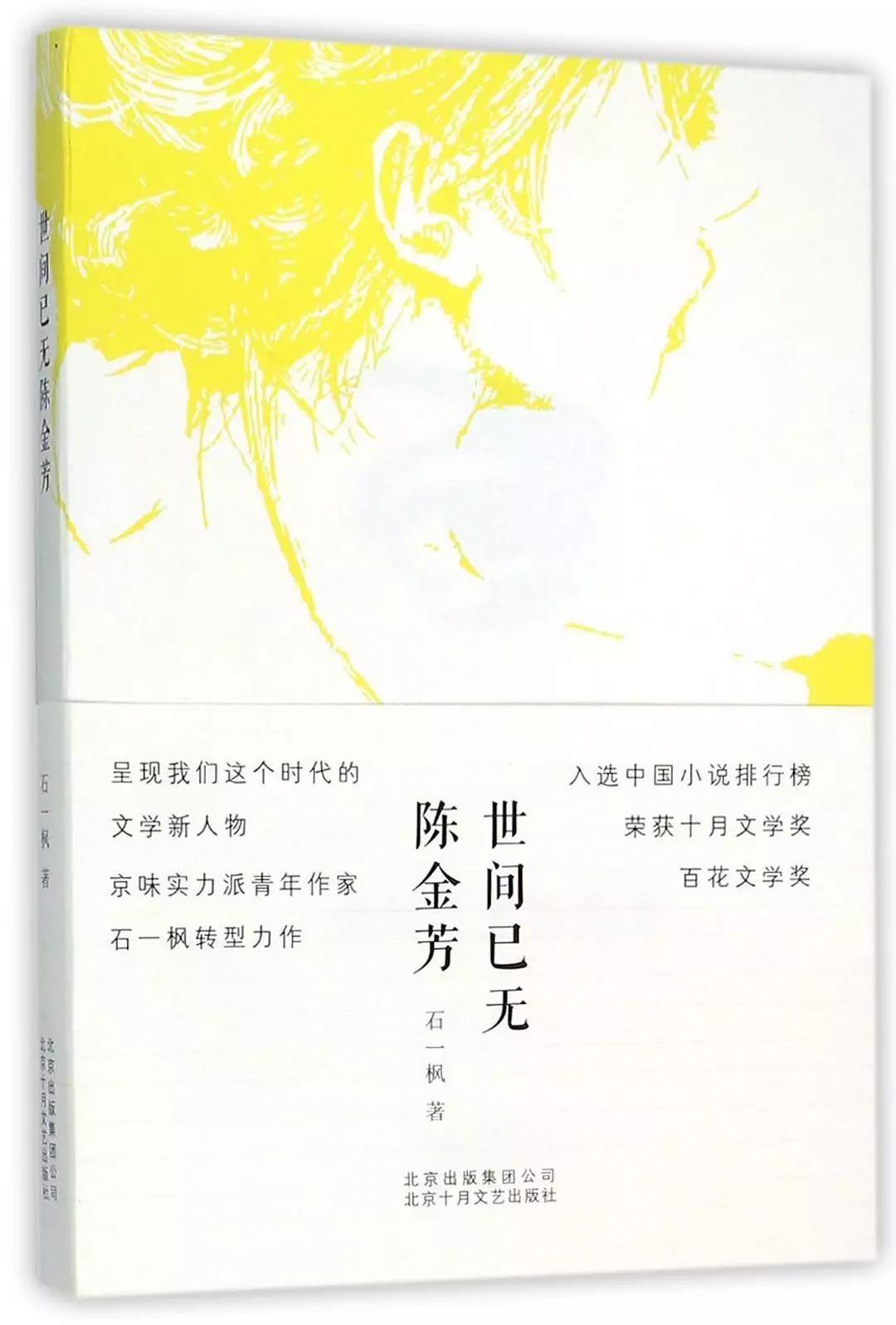
石一枫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
另外,就像梁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总是习惯把城市和乡村想成二元对立的关系。好像中国人很习惯这样想,尤其是近代的中国人。新中国就是把人们分成不同的户口。户口是很简单的,把城市和乡村对立来想。不止在中国,我觉得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的想法,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可能每个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想象,因为城市里工厂的工业化生产,是与农村的生活环境相对的。
刚才梁老师也谈到了,我们对于乡村的两种想象,一种是鲁迅式的,另一种就是沈从文式的。鲁迅是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我们国家为什么弱?中国为什么强不起来?是因为乡村里都是阿Q那样的人。沈从文是完全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想,他不太想国家强不强,他想的是我为什么不幸福。我为什么不幸福?因为我离开了乡村。这两种想象,应该说都是偏颇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文化人也好,虽然大部分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但是既往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书写,很少有人能够提供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乡村样貌和乡村本质。
如果站在今天中国的角度,我们真的需要把城乡分开想象吗?有的时候未见得。原来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的很多障碍,今天已经不是障碍了,比如教育障碍已经不是障碍,技术障碍也不是障碍,经济上的障碍也在飞速缩小。以后,面对城市和乡村,需要有新的想象方式,或者新的书写方式。
对乡村的负面想象让我们丧失了故乡
梁鸿:一枫用“爆炸”这个词特别恰当,曾经有一句话说“中国四十年走了西方四百年的道路”。“四十年浓缩四百年”,是什么概念?因为速度太快了,里面可能压缩了无数无数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的方向性问题,我们只是探讨在这样的状态上,人的精神状态和观念的问题。
城乡二元对立的相对固定化的观念,其实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从而了影响政策的制订,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我曾经跟着一个团体,到台湾呆了十几天时间,我们发现在台湾的很多学校里面,都有一个“在地教育”。它一方面指的是学校教育,比如在中小学课堂里面,每人有一本地理课本,是关于本地的山川样貌,比如说雪山、古城、周边河流的走向、山川的来源等等。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他会对他自身生活的地方非常熟悉,他知道这个地方的山是从哪来,这个水从哪来,它经历多长的时间,它是多么美。我们稍微想想我们乡村的孩子,我们爱自己的家乡吗?我们是不爱的,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你一定要离开农村,要考上学,才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你不能埋怨农民不爱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们整个国度都不爱这个乡村,你怎么能要求农民去爱呢?
台湾民间还有很多类似老年大学这样的地方,这些热心人会整理本地的戏曲、历史掌故等等。如果一条河被污染了,当地人就会往上找,是在哪个地方把污水排出来的,一直找到那家工厂。这就是当地人做的事情,不单单是政府来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是会非常热爱、了解这个地方的。
关于乡土,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我写梁庄,梁庄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生活20年,我们村庄有一条大河,我是非常喜欢的,可我真正了解那条河吗?我是在过了三十多年之后,才再去看那条河,回去找这条河的来龙去脉。如果小时候我受到了类似的教育,可能很早就有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每个人都无家可归,我们的故乡沦陷。”这句话太俗气,但是它的确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一种生活形态。你一年不回家,回到家里,这条河没了,两年不回家,整个村庄都没了。我曾经在一个乡村当过小学老师,教了三年,我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但是前年回去,我突然发现,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后来我找当年我的学生,让他给我带路,他自己也说不清了。

梁鸿著作《中国在梁庄》
在这样一种形态之下,人的内心,会有非常微妙的动摇之感。它不会给你造成打击,你还在生活,你该干嘛干嘛,它不是显象层面的动摇,它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动摇。比如一个老人倒地没有人敢扶,我可能也不敢扶,怕他万一讹我怎么办。大家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因为一种基本信任没有了,这种基本信任来源的共同体没有了。这个共同体不是指乡村,而是指,由乡村整体的动摇,带来的许多观念的动摇。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农村经济学家的会,有一位研究农村的专家,当时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他的开场白说,如果有一天在正式场合里,中国人都能穿西服、打领带,我们的社会肯定是非常棒的社会。他是研究农村社会学的,他说中国农村太有问题了,端一碗饭走四五家,哪有隐私可言。他意思是农村大家串门,中午吃饭可能到你家坐坐,到我家坐坐,吃一碗饭可能吃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可能聊一些新闻什么的。他这个说法可能也是对的,没有隐私。但是村庄也有某种亲密感。我们现在总是把村庄负面的东西夸大,但实际上文化里有某些积极的东西,是可以源远流长的,现在却被挤压掉了。他还说,北京发展不好,是因为那些城中村很难拆迁,使得北京面貌非常落后。
他发言完刚好我发言,我当时也不客气,我说中国人没有自己传统的服饰,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作为炫耀,那就有问题了。在印度,人家在正式场合还穿长衫、白裤子,女的还穿纱丽,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你不能就因此说人家落后。在农村,端一碗饭走四家,固然没有隐私,但是城市里面住了十年谁也不认识谁,就一定是好的吗?我们一个楼里面有十户人家,谁也不认识谁,甚至连招呼都不愿意打,就好吗?楼里面一个人死掉,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人知道,就好吗?在农村,你突然间闭门闭户,大家一定好奇是怎么回事。那也不见得是坏的事情。最后,我说北京幸亏还有城中村在,还能够使得一些农民工、打工者、普通白领,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生活在这些地方。
有一本书叫《蚁族》,讲前些年北京的唐家岭,那个地方聚集了几乎十万普通的年轻人,每天早上挤车,几趟都挤不上。后来因为《蚁族》这本书出来后影响比较大,政府说唐家岭一定要改造。一个城郊农村被改造之后要盖什么?要盖高档小区,要盖高档商场,这些高档商场和小区,肯定不是为普通打工者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变好了,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住到了唐家岭后面的一个村庄,要奔波更远的路程。
我说,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是用一种分离的观点在看他们,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人也是跟我们同在的。我觉得这是有歧视的观念,持这样的观念来理解乡村肯定有很多问题。
石一枫:确实,一些本来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真得重新反思、衡量它。比如我们觉得,来自乡村的人必须要出去,是中国90%以上的乡村青年都会有的想法。这个观念有一个又一个的标志性文学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它讲什么故事?就是必须要出去。再往后,几乎每个当代作家可能都写过类似的题材。但有的时候真觉得必须要出去吗?
类似的困惑和再反思,也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的,刚才梁老师说台湾,台湾的确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时期,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济好的时候,台湾人也是有“必须要出去”的想法。我以前看日本电影,日本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的日本乡村,有一套典雅的、有美感的乡村生活体系。不愿意离开的人,在这个地方呆得很好。他们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已经非常小,已经过了一定要出去的阶段。你想换个活法没问题,你选择大城市的生活,收入,生活便捷,但生存压力大,人与人之间冷淡,这是有得有失,是你自己跟自己做的一个交易,你享受这个交易的好的地方,也承受这个交易不好的地方。
另外,我们总是用城市改造乡村,总是这边强那边弱。其实中国古代反而是乡村改造城市,因为所有城市精英全是乡村精英,京官全是科举考过去的,这些江南才子、北方望族的后代,告老还乡之后再回乡下,四处建园林。那时候,城乡观念跟现在不一样,双方谁处在强和弱的地位上不好说。我们现在强弱之间的差别特别大,而且我们总是在想改造乡村,我有时候也奇怪,你有什么资格改造人家?瞧瞧你脏乱差的样,城市搞这么难看,你也配改造人家吗?
其实对于城市和乡村,还有第三个想象,就是社会主义想象。十七年文学里,还想象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乡村,想象了不起的梁生宝这种人,开天辟地,创业史,朝阳沟,金光大道,就是想象这样的乡村,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想象,在某种意义来说是真的想象,因为等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八十年代开始重新写作乡村之后,发现这样的农民全都没了,作品里面没有,在生活里面也没有。原来所有中国农民都是梁生宝,怎么现在一个梁生宝也不剩了,梁生宝都跑到哪去了,怎么都变成《桑树坪记事》了?我们刚才说的鲁迅的想象或者沈从文的想象,多少有点真实的影子,但梁生宝的真实成分更少,更多是美好的期望。
关于乡村,我们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想法,我们需要站远一点,思考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它怎么就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它。凡事多想一步,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可能会深一点。
睁开眼睛,观察当下的城乡
梁鸿:这几天来到丽江,我感到了一种迷人的自信,人们对这片土地是自信的,对文化是自信的。昨天我见到恒裕公的主人,他说你给我一百万都不卖,我这个房子租一百万都不租。他热爱这个房子、他的祖屋,他也热爱他的祖先,他实际上是热爱他生活的这个地方。这种自信,使得我们每个人想睁开眼睛打量自己生活的地方。现在总说诗和远方,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每个人的生活内部都有很多很多空间,你的家人,你和家人的关系,你跟你自己房屋的关系,你跟你身后这条河的关系,都是非常美好的关系,如果能够想通这一点,其实不必被整个成功学的社会所改造,这种成功学,真的是一种资本主义逻辑,你必须有金钱、豪宅,才是成功人士,才有可能被尊重。传统社会里的“安之若素”,已经变成可笑的词语,你贫穷就是不行,你贫穷就是要挨打。原来,在一个社会里面,一个人道德上很有自己的坚守,很有自己的品格,那是非常受尊重的。但是这种最朴素的存在,也慢慢都没有了。
不光是农民,不光是我们生活在当地的人,我自己最想说的就是,你要看看身边的人,对于写作,这点非常重要。写作不要被大的概念所裹挟,你要睁开眼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普通生活的人,也是一样的,你不写作,但你要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美的所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如果要写乡村的话,一定要看看身边真正的人的存在,这才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形态,这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石一枫:梁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不光是对于作家同行,对于每个生活中的人都是这样,写作就是琢磨人,如果说琢磨几个概念,或者琢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个不是真正的写作。
过去一天24小时,可能20小时琢磨吃,4个小时琢磨人。现在中国人,尤其丽江人,吃饭早就不成问题,我觉得24小时除了睡觉可能全都在琢磨人,天生都适合写作。在生活里面琢磨人越多的人,越适合写作。我到很多中国的旅游目的地,我发现当地人文气最强的地方,还真就是丽江,好像每个人都很风雅。你们的生活已经是我们的诗和远方了,但是你们还在想诗和远方,多么可敬。所以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学习一种生活态度、生活姿态。
客观地说,经济发展有一点好,在解决吃的问题之后,有这种面貌的人的确变多。我前一阵去浙江台州,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了一个书院里面,一个留着胡子、留着长发的书院主人出来迎接,说我除了写书法还画画,你可以参观一下我画的画。我在很多经济相对好一点的乡村,都会见到这样的人,有喜欢书画的,喜欢烧窑的,各种各样的,物质自足,精神也自足。过去中国人总是为物质自足发愁,后来又为精神自足发愁,这是关乎到生活幸福的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疑问。
问答环节
沈从文的乡土写作是一种美的教育
问题:我想了解老师们对于沈从文《边城》的评价。
梁鸿:沈从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沈从文不单单塑造所谓的田园式乡村,他还特别关注个人性,他特别打开个人。他跟鲁迅是两个方向,鲁迅打开人的痛苦,让你反思;沈从文是告诉你,你的人生里面还有这么优美的东西,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这么优美的东西。所以你读沈从文的《边城》,有非常美好的感觉。我第一次读沈从文,可能是十四五岁,当时读到结尾,“那个人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觉得非常怅惘和感动,不单单打开了情感,也打开了你对自己的思考,再往深处讲打开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当然,乡村图景是另外层面的解读,重要的是,他打开个人内部存在的可能的美好,打开了乡土社会内部可能的精神形态,打开了一种人情的美、人性的美、风俗的美,彼此之间相互谅解的美。小说家有三个功能,一个是教育家,一个是讲故事的人,一个是魔术师。我觉得教育家可能就是指这一点,他让你意识到这是美的,你会朝着这个方向,哪怕有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向往,也是好的。
对于古城民俗,要保护和改造并施
问题:很多丽江人都觉得古城商业化太严重了,以前纳西文化以及七八十年代的风格不复存在,到处都是酒吧街、商业街之类的。老师谈到的乡土文化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保存下来?
石一枫:这个问题我明白了,就是怎么一边挣钱一边保护文化财产。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有两个向往浪漫的人一定要去的地方,一个是丽江,一个就是湘西凤凰。但是这两个地方现在都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我的感觉,二者很多时候不可兼得。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只要一个城市有名了,它变成一个游客必去的地方,它一定会变得跟原来不一样。我们意识到它一定要变,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这个时代,改造是正常的事情。在不破坏民俗的前提下,改造好古城,比把昨天的东西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更重要。

梁鸿、石一枫、吕约同丽江文学爱好者合影留念
(编辑:moyuzhai)

编者按
6月20日上午,“十月作家居住地・丽江古城”第二场名家讲堂在丽江古城雪山书院成功举办。本次活动由十月文学院、世界文化遗产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共同主办。
著名学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首位入住“十月作家居住地・丽江古城”的作家梁鸿,和著名作家、《当代》杂志主编助理石一枫,围绕着“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展开了别有生趣又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对谈。十月文学院常务副院长吕约,丽江古城保护管理局副局长和堂出席了本次活动,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丽江市高等师范专科学校、丽江市文学界专家学者和丽江市作家协会成员共同参加了本次活动。
梁鸿和石一枫为大家梳理了传统观念中对乡土文化的两种封闭式的想象类型,呼吁大家对固有的城乡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进行反思,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乡土写作拥有塑造民族精神共同体的重大意义。梁鸿指出,乡村生活本质上是人的生活,有流动的需求和渴望,因此不管是愚昧落后亦或田园牧歌式的想象,都忽略了乡村流动性和开放性,应该用城乡相互生成的概念来代替传统二元对立的想象。石一枫认为当代中国城市的发展是偶发和爆炸性的现象,人们应该打破城市改造乡村的文化等级秩序,他从世界文学的角度谈到了人们对土地内在的依恋和回归情节,认为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需要一种新的书写方式和美学规范。
城与乡并非二元对立,而是互相生成
梁鸿:我一直对丽江充满向往,这两天去了白沙古镇、束河古镇,也有了一些想法。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社会最大的主题就是改造乡村。不管是文化改造、经济改造还是农民进城,都能延伸出一系列问题,这些问题不单单是政治学家、经济学家的问题,其实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问题,精神状态的问题,实际上当代作家是非常关注这个层面的。对于普通老百姓,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潮之中,也需要考虑怎样去适应,去看待,或者思考自己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从现代以来,乡土中国经历了一个被改造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关于乡土的想象。我们最熟悉的一种想象可能是,认为乡村是古老的、封闭的、一潭死水的,跟我们现代生活是完全分离的。还有一种关于乡土的想象是桃花源式的,大家都知道陶渊明,田园诗,从中感到乡土是非常非常美的。
关于乡土的想象,一直朝这两个维度发展,一方面觉得乡土是封闭的、固守的,我们需要去改造它,需要让它跟现代生活接轨,另外一种觉得乡土是田园诗一样的,它需要我们去维护、去坚守,不要变动它,或者它成为每个人心中一个古老的梦。但是就我的理解而言,我觉得这两种想象都是非常狭窄的或者片面的,都是把乡土世界、乡土文化、乡土的精神内涵做了一个固定的、悬于我们生活之上的思考。
其实在我的观察和思索里,乡土社会从来都不是完全封闭的,乡土社会里面的农民、乡绅、普通生活的人,都是对生活充满向往的。即使中国最古老的乡村,保持着中国社会最古老的组织形态,它仍然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因为有人,所以都有向外流动的冲动和渴望。这也是近几十年来农民进城的重要原因。并非是改革开放一系列政策以后,大家才知道出门打工挣钱,其实农民一直有这个愿望。
我们的当代文化、政治发展方向,把城乡二元对立变得非常固化。我曾经查过国务院1950-1959年关于农民的一个政策,阻止农民盲目进城。这群农民简称盲流。实际上,在一年年反复的阻止过程中,我们把“城市”和“乡村”作为二元对立的概念隔离开了,所以才有文化层面、政治层面的这些观念的生成。我们看到很多文学写作里面,写到农民是多么保守,多么愚昧,在城市里面多么不适应,其实并非是天然的,这里面有非常现实的政治原因和精神原因。
为什么在丽江刚好说这个话题?丽江是一个旅游的城市,作为外地人,首先我们觉得丽江自然风景非常诱人,它的阳光、它的雪山、它的整体氛围这样美好。在这些年的发展过程中,丽江可能给大家塑造了一个梦,这个梦里面有两点:一个梦是所谓的田园诗,你来到这个地方,像桃花源一样非常美,你可以慢生活,你可以寻找那种悠远的关于古老生活形态的梦想。还有一个是所谓的逃离,城市人要逃离城市的繁忙,来到这个地方。这两种想象,也是延续了关于乡土的比较单一的、封闭的想象,这样一来,丽江是非常被动的,我们把丽江作为一个被动的田园风光形态的存在,而忽略了丽江人民或者丽江本地生活形态的开放性。
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想象,这展现了我们社会一种偏执的观念,我们把乡土作为一个固定、封闭的东西去处理它、去思考它,这是非常大的问题。石一枫刚好写过一些关于农民进城的作品,比如《世上已无陈金芳》,一直思考关于农民,关于乡土社会跟城市之间的冲突,关于乡土的生成的问题。我特别喜欢用“乡土生成”取代“城乡二元对立”这个词,因为“二元对立”是排斥性的,“乡土生成”是生长性的,是彼此在塑造的。
我当年写《出梁庄记》,因为要做调查,跑了好多城市,我发现实际上农民的形态,完全是在城市化进程中被塑造、生成出来的,并非天然就是愚昧、麻木的。据我的理解而言,乡村里面必然承载着一个人最古老的梦想,因为跟大地相关的东西总是很让人向往,但另一方面,这个大地也是行进在时代中的大地,它不是跟时代无关的大地,这才是比较开放的观点。
石一枫:我从小到大一直住在北京,也没出过北京,要说真正的乡村是什么样,我并没有看过。但后来想想,我的生活里面,乡村的因素也很多。中国的城市很特殊,发展的速度奇快无比。我们回想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比如丽江市,可能还叫丽江地区,想到昆明,再想到北京,其实根本不是我们今天意义上的城市。
我从小到大住的地方,在今天北京叫西四环路。我上小学的时候,小学老师明确告诉我们这里是郊区。北京的四环路,三十年前全是农田,今天想起来是很沧海桑田的。北京很有意思的一个地方是,你今天看到高楼大厦、很现代化的地方,它的名字都土的要命。比如中关村,为什么叫“村”?三十年前,它就是一个农田,就是一个村,有人在那里种地。比如太阳宫,今天是一个高级住宅区,挨着望京,10万块钱一平米,但是当年的太阳宫就是农田。
从我这一代人的经历可以看出来,第一,我们的城市在我们国家历史上,是偶发的、特殊的现象,是爆炸式出现的。前二十年,目睹着北京、上海、广州三个炸弹,在我们国家版图上炸开,把乡村全都炸成城市,炸成高楼大厦,炸成机场、高铁站,我们现在依然目睹这样的爆炸继续进行。武汉也在爆炸,郑州也在爆炸,合肥也在爆炸,今天所有炒房团炒到哪里,哪里就是爆炸最热闹的地方。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其实是偶发的、突然的,甚至仓促的进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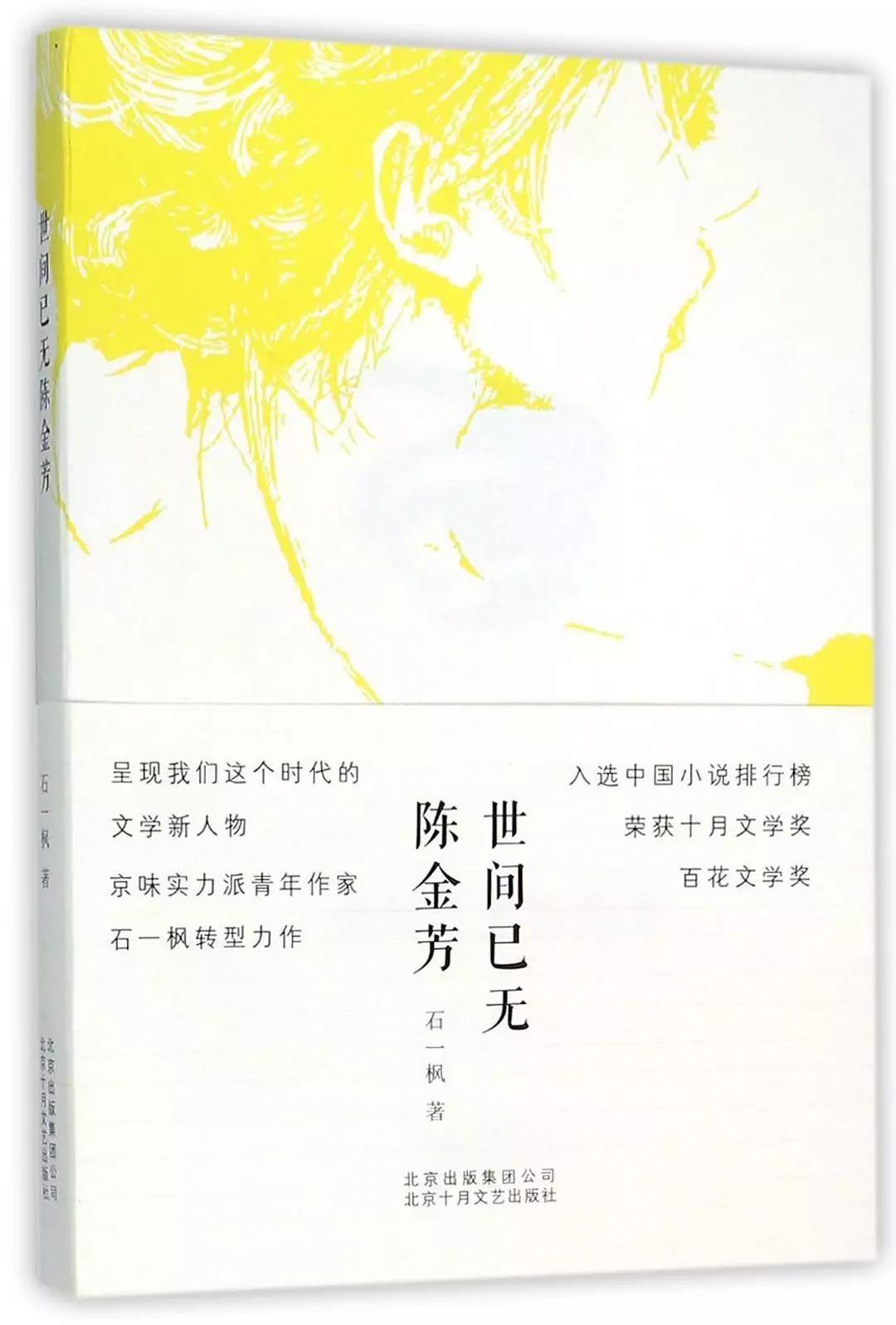
石一枫作品《世间已无陈金芳》
另外,就像梁老师刚才说的,我们总是习惯把城市和乡村想成二元对立的关系。好像中国人很习惯这样想,尤其是近代的中国人。新中国就是把人们分成不同的户口。户口是很简单的,把城市和乡村对立来想。不止在中国,我觉得把城市和乡村对立起来的想法,其实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物。可能每个经历过现代化的国家,都有这样的想象,因为城市里工厂的工业化生产,是与农村的生活环境相对的。
刚才梁老师也谈到了,我们对于乡村的两种想象,一种是鲁迅式的,另一种就是沈从文式的。鲁迅是在国家民族的立场上思考,我们国家为什么弱?中国为什么强不起来?是因为乡村里都是阿Q那样的人。沈从文是完全站在个人的立场上想,他不太想国家强不强,他想的是我为什么不幸福。我为什么不幸福?因为我离开了乡村。这两种想象,应该说都是偏颇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也好,文化人也好,虽然大部分都是从乡村走出来的,但是既往的知识分子对乡村的书写,很少有人能够提供一种全面的、客观的、令所有人都信服的乡村样貌和乡村本质。
如果站在今天中国的角度,我们真的需要把城乡分开想象吗?有的时候未见得。原来把城市与乡村分开的很多障碍,今天已经不是障碍了,比如教育障碍已经不是障碍,技术障碍也不是障碍,经济上的障碍也在飞速缩小。以后,面对城市和乡村,需要有新的想象方式,或者新的书写方式。
对乡村的负面想象让我们丧失了故乡
梁鸿:一枫用“爆炸”这个词特别恰当,曾经有一句话说“中国四十年走了西方四百年的道路”。“四十年浓缩四百年”,是什么概念?因为速度太快了,里面可能压缩了无数无数的问题没有解决。但我们在这里不讨论它的方向性问题,我们只是探讨在这样的状态上,人的精神状态和观念的问题。
城乡二元对立的相对固定化的观念,其实影响了我们的思维模式,从而了影响政策的制订,影响了我们对自己的理解。我曾经跟着一个团体,到台湾呆了十几天时间,我们发现在台湾的很多学校里面,都有一个“在地教育”。它一方面指的是学校教育,比如在中小学课堂里面,每人有一本地理课本,是关于本地的山川样貌,比如说雪山、古城、周边河流的走向、山川的来源等等。在这个教育的过程中,他会对他自身生活的地方非常熟悉,他知道这个地方的山是从哪来,这个水从哪来,它经历多长的时间,它是多么美。我们稍微想想我们乡村的孩子,我们爱自己的家乡吗?我们是不爱的,因为我们从小受到的教育,是你一定要离开农村,要考上学,才可能过上好的生活。你不能埋怨农民不爱自己的家乡,因为我们整个国度都不爱这个乡村,你怎么能要求农民去爱呢?
台湾民间还有很多类似老年大学这样的地方,这些热心人会整理本地的戏曲、历史掌故等等。如果一条河被污染了,当地人就会往上找,是在哪个地方把污水排出来的,一直找到那家工厂。这就是当地人做的事情,不单单是政府来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其实是会非常热爱、了解这个地方的。
关于乡土,我们到底知道多少?我写梁庄,梁庄是我的老家,我在那里生活20年,我们村庄有一条大河,我是非常喜欢的,可我真正了解那条河吗?我是在过了三十多年之后,才再去看那条河,回去找这条河的来龙去脉。如果小时候我受到了类似的教育,可能很早就有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曾经有一句流行的话:“每个人都无家可归,我们的故乡沦陷。”这句话太俗气,但是它的确是我们这个大时代的一种生活形态。你一年不回家,回到家里,这条河没了,两年不回家,整个村庄都没了。我曾经在一个乡村当过小学老师,教了三年,我对那个地方特别有感情。但是前年回去,我突然发现,怎么找也找不着了。后来我找当年我的学生,让他给我带路,他自己也说不清了。

梁鸿著作《中国在梁庄》
在这样一种形态之下,人的内心,会有非常微妙的动摇之感。它不会给你造成打击,你还在生活,你该干嘛干嘛,它不是显象层面的动摇,它是内在的精神层面的动摇。比如一个老人倒地没有人敢扶,我可能也不敢扶,怕他万一讹我怎么办。大家为什么有这种观念?因为一种基本信任没有了,这种基本信任来源的共同体没有了。这个共同体不是指乡村,而是指,由乡村整体的动摇,带来的许多观念的动摇。
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农村经济学家的会,有一位研究农村的专家,当时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他的开场白说,如果有一天在正式场合里,中国人都能穿西服、打领带,我们的社会肯定是非常棒的社会。他是研究农村社会学的,他说中国农村太有问题了,端一碗饭走四五家,哪有隐私可言。他意思是农村大家串门,中午吃饭可能到你家坐坐,到我家坐坐,吃一碗饭可能吃一个小时,那一个小时可能聊一些新闻什么的。他这个说法可能也是对的,没有隐私。但是村庄也有某种亲密感。我们现在总是把村庄负面的东西夸大,但实际上文化里有某些积极的东西,是可以源远流长的,现在却被挤压掉了。他还说,北京发展不好,是因为那些城中村很难拆迁,使得北京面貌非常落后。
他发言完刚好我发言,我当时也不客气,我说中国人没有自己传统的服饰,这是很悲哀的事情,没有也就没有了,但是你如果把这个作为炫耀,那就有问题了。在印度,人家在正式场合还穿长衫、白裤子,女的还穿纱丽,保留了自己的民族服饰,你不能就因此说人家落后。在农村,端一碗饭走四家,固然没有隐私,但是城市里面住了十年谁也不认识谁,就一定是好的吗?我们一个楼里面有十户人家,谁也不认识谁,甚至连招呼都不愿意打,就好吗?楼里面一个人死掉,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人知道,就好吗?在农村,你突然间闭门闭户,大家一定好奇是怎么回事。那也不见得是坏的事情。最后,我说北京幸亏还有城中村在,还能够使得一些农民工、打工者、普通白领,用比较便宜的价格,生活在这些地方。
有一本书叫《蚁族》,讲前些年北京的唐家岭,那个地方聚集了几乎十万普通的年轻人,每天早上挤车,几趟都挤不上。后来因为《蚁族》这本书出来后影响比较大,政府说唐家岭一定要改造。一个城郊农村被改造之后要盖什么?要盖高档小区,要盖高档商场,这些高档商场和小区,肯定不是为普通打工者准备的。这个地方是变好了,但是对于这些人来说,他们住到了唐家岭后面的一个村庄,要奔波更远的路程。
我说,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是用一种分离的观点在看他们,你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人也是跟我们同在的。我觉得这是有歧视的观念,持这样的观念来理解乡村肯定有很多问题。
石一枫:确实,一些本来认为天经地义的观念,真得重新反思、衡量它。比如我们觉得,来自乡村的人必须要出去,是中国90%以上的乡村青年都会有的想法。这个观念有一个又一个的标志性文学作品,比如《平凡的世界》,它讲什么故事?就是必须要出去。再往后,几乎每个当代作家可能都写过类似的题材。但有的时候真觉得必须要出去吗?
类似的困惑和再反思,也是每个国家和地区都经历过的,刚才梁老师说台湾,台湾的确也经历过一个类似的时期,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经济好的时候,台湾人也是有“必须要出去”的想法。我以前看日本电影,日本也有这样的想法。但是现在的日本乡村,有一套典雅的、有美感的乡村生活体系。不愿意离开的人,在这个地方呆得很好。他们乡村和城市的区别已经非常小,已经过了一定要出去的阶段。你想换个活法没问题,你选择大城市的生活,收入,生活便捷,但生存压力大,人与人之间冷淡,这是有得有失,是你自己跟自己做的一个交易,你享受这个交易的好的地方,也承受这个交易不好的地方。
另外,我们总是用城市改造乡村,总是这边强那边弱。其实中国古代反而是乡村改造城市,因为所有城市精英全是乡村精英,京官全是科举考过去的,这些江南才子、北方望族的后代,告老还乡之后再回乡下,四处建园林。那时候,城乡观念跟现在不一样,双方谁处在强和弱的地位上不好说。我们现在强弱之间的差别特别大,而且我们总是在想改造乡村,我有时候也奇怪,你有什么资格改造人家?瞧瞧你脏乱差的样,城市搞这么难看,你也配改造人家吗?
其实对于城市和乡村,还有第三个想象,就是社会主义想象。十七年文学里,还想象了一个社会主义新人的乡村,想象了不起的梁生宝这种人,开天辟地,创业史,朝阳沟,金光大道,就是想象这样的乡村,非常有意思。而且这个想象,在某种意义来说是真的想象,因为等到“文革”结束之后,我们八十年代开始重新写作乡村之后,发现这样的农民全都没了,作品里面没有,在生活里面也没有。原来所有中国农民都是梁生宝,怎么现在一个梁生宝也不剩了,梁生宝都跑到哪去了,怎么都变成《桑树坪记事》了?我们刚才说的鲁迅的想象或者沈从文的想象,多少有点真实的影子,但梁生宝的真实成分更少,更多是美好的期望。
关于乡村,我们有那么多天经地义的想法,我们需要站远一点,思考这个想法是怎么来的,它怎么就成为我们根深蒂固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可能摆脱它。凡事多想一步,我们对自己生活的认识可能会深一点。
睁开眼睛,观察当下的城乡
梁鸿:这几天来到丽江,我感到了一种迷人的自信,人们对这片土地是自信的,对文化是自信的。昨天我见到恒裕公的主人,他说你给我一百万都不卖,我这个房子租一百万都不租。他热爱这个房子、他的祖屋,他也热爱他的祖先,他实际上是热爱他生活的这个地方。这种自信,使得我们每个人想睁开眼睛打量自己生活的地方。现在总说诗和远方,我特别不喜欢这句话。每个人的生活内部都有很多很多空间,你的家人,你和家人的关系,你跟你自己房屋的关系,你跟你身后这条河的关系,都是非常美好的关系,如果能够想通这一点,其实不必被整个成功学的社会所改造,这种成功学,真的是一种资本主义逻辑,你必须有金钱、豪宅,才是成功人士,才有可能被尊重。传统社会里的“安之若素”,已经变成可笑的词语,你贫穷就是不行,你贫穷就是要挨打。原来,在一个社会里面,一个人道德上很有自己的坚守,很有自己的品格,那是非常受尊重的。但是这种最朴素的存在,也慢慢都没有了。
不光是农民,不光是我们生活在当地的人,我自己最想说的就是,你要看看身边的人,对于写作,这点非常重要。写作不要被大的概念所裹挟,你要睁开眼看看你身边的人是什么状态。我们普通生活的人,也是一样的,你不写作,但你要看看自己的生活,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美的所在。我经常告诫自己,如果要写乡村的话,一定要看看身边真正的人的存在,这才是千姿百态、多种多样的形态,这也是我想分享给大家的。
石一枫:梁老师刚才说的,我觉得不光是对于作家同行,对于每个生活中的人都是这样,写作就是琢磨人,如果说琢磨几个概念,或者琢磨一些莫名其妙的东西,那个不是真正的写作。
过去一天24小时,可能20小时琢磨吃,4个小时琢磨人。现在中国人,尤其丽江人,吃饭早就不成问题,我觉得24小时除了睡觉可能全都在琢磨人,天生都适合写作。在生活里面琢磨人越多的人,越适合写作。我到很多中国的旅游目的地,我发现当地人文气最强的地方,还真就是丽江,好像每个人都很风雅。你们的生活已经是我们的诗和远方了,但是你们还在想诗和远方,多么可敬。所以我们应该向你们学习,学习一种生活态度、生活姿态。
客观地说,经济发展有一点好,在解决吃的问题之后,有这种面貌的人的确变多。我前一阵去浙江台州,看社会主义新农村。到了一个书院里面,一个留着胡子、留着长发的书院主人出来迎接,说我除了写书法还画画,你可以参观一下我画的画。我在很多经济相对好一点的乡村,都会见到这样的人,有喜欢书画的,喜欢烧窑的,各种各样的,物质自足,精神也自足。过去中国人总是为物质自足发愁,后来又为精神自足发愁,这是关乎到生活幸福的问题,究竟能不能解决?我个人感觉还是一个疑问。
问答环节
沈从文的乡土写作是一种美的教育
问题:我想了解老师们对于沈从文《边城》的评价。
梁鸿:沈从文我是非常喜欢的,因为沈从文不单单塑造所谓的田园式乡村,他还特别关注个人性,他特别打开个人。他跟鲁迅是两个方向,鲁迅打开人的痛苦,让你反思;沈从文是告诉你,你的人生里面还有这么优美的东西,我们的社会里面还有这么优美的东西。所以你读沈从文的《边城》,有非常美好的感觉。我第一次读沈从文,可能是十四五岁,当时读到结尾,“那个人也许回来,也许不回来”,觉得非常怅惘和感动,不单单打开了情感,也打开了你对自己的思考,再往深处讲打开了你对自己生活的思考。当然,乡村图景是另外层面的解读,重要的是,他打开个人内部存在的可能的美好,打开了乡土社会内部可能的精神形态,打开了一种人情的美、人性的美、风俗的美,彼此之间相互谅解的美。小说家有三个功能,一个是教育家,一个是讲故事的人,一个是魔术师。我觉得教育家可能就是指这一点,他让你意识到这是美的,你会朝着这个方向,哪怕有一点点的努力、一点点的向往,也是好的。
对于古城民俗,要保护和改造并施
问题:很多丽江人都觉得古城商业化太严重了,以前纳西文化以及七八十年代的风格不复存在,到处都是酒吧街、商业街之类的。老师谈到的乡土文化如何在这种情形之下保存下来?
石一枫:这个问题我明白了,就是怎么一边挣钱一边保护文化财产。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有两个向往浪漫的人一定要去的地方,一个是丽江,一个就是湘西凤凰。但是这两个地方现在都面临着过度商业化的问题。我的感觉,二者很多时候不可兼得。世界各地都是这样,只要一个城市有名了,它变成一个游客必去的地方,它一定会变得跟原来不一样。我们意识到它一定要变,但是我们可以让它变得更好。这个时代,改造是正常的事情。在不破坏民俗的前提下,改造好古城,比把昨天的东西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更重要。

梁鸿、石一枫、吕约同丽江文学爱好者合影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