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沃土》(长篇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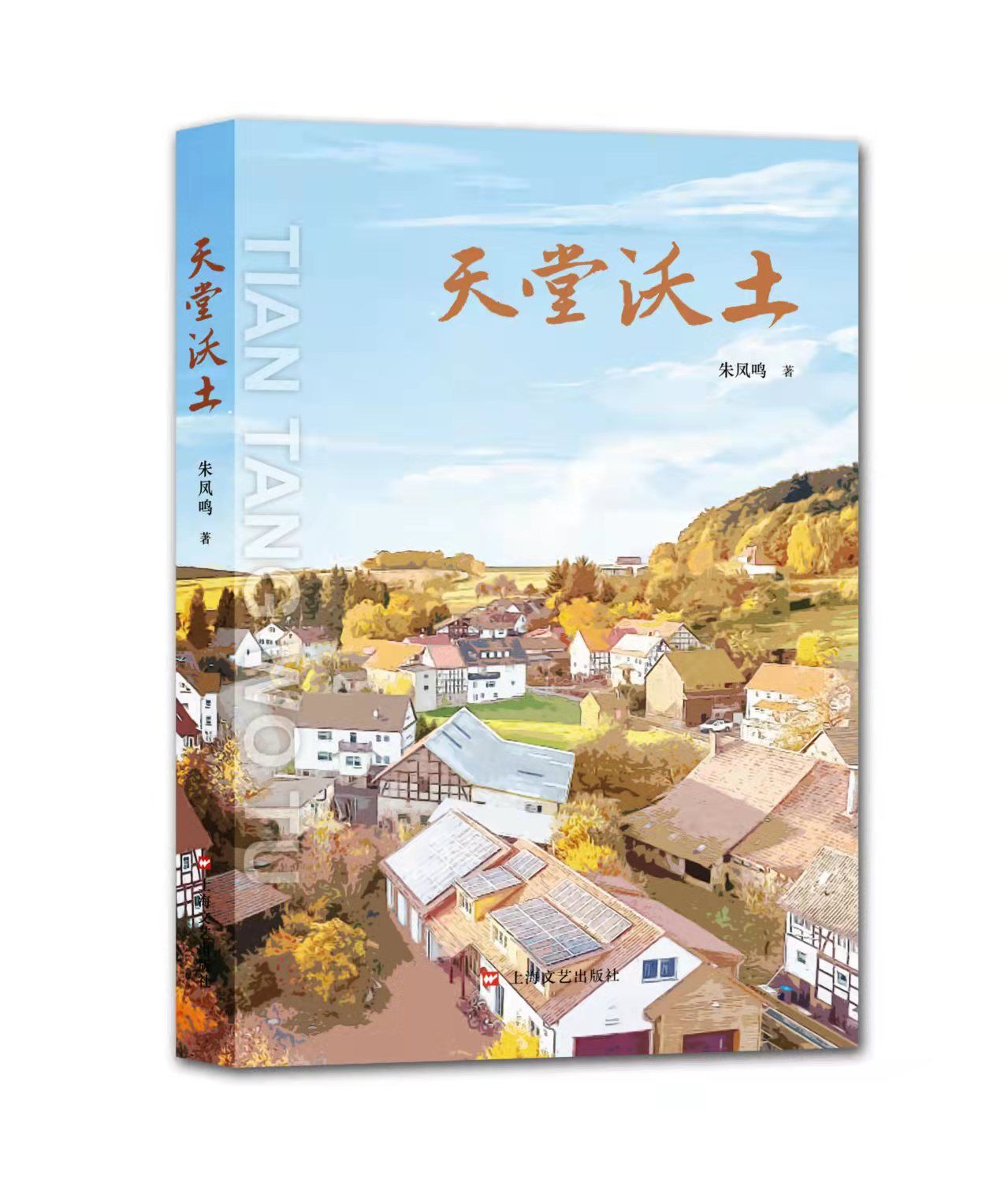
一、基本信息
书名:长篇小说《天堂沃土》
作者:朱凤鸣
出版社: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321-8111-7
定价:88.00元
二、内容简介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太仓作家朱凤鸣历时三年创作的长篇小说《天堂沃土》,以太仓农村为背景,以鹤塘镇群星生产队(村民小组)三大家族中与共和国同龄的三个主人公朱建国、张忠良、夏永生的矛盾纠葛和成长经历为主线,反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苏南农村及家庭发生翻天覆地巨变的历史进程,歌颂真善美,鞭挞假丑恶。作品探索“无界文学”写作,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和与时俱进的时代感,以激励人们更加热爱中国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热爱家乡,坚定跟共产党走,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梦作贡献。这是他出版的第17部文学著作。
三、后记
2018年5月12日下午,我在项门新村自家的农村别墅书房内打开电脑,开始了长篇小说《天堂沃土》的创作。电脑屏幕上是我上幼儿园的孙儿在上海新湖明珠城小游园的一幅照片,背景是两幢住宅高楼,边上是微波荡漾的小池塘,池塘边绿树成荫,鲜花盛开,身穿红色上衣的孙儿微笑着看着我,仿佛在对我说,爷爷你快写吧,我正等着看呢。是的,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就是写给他们这辈人看的,六七十年前的事,如果我再不写,他们就不会知道。于是,我开始写下第一行字:1949年5月12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又是一个特殊的日子……写作间隙,随意看看院子的西花坛和南花坛中十棵开得正旺的月季花,大红、粉红、金黄的花朵在绿叶衬托下显得格外鲜艳,几只白蝴蝶在花朵间翩翩起舞,让我的心情非常轻松,既观赏着自然的美景,又享受着创作的愉悦。
因为我的小说开头就是从1949年5月12日开始的,那确实是一个平常的日子,又是一个特殊的日了。这天,主人公朱建国伴随着解放太仓的激烈枪声出生了。70年,对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但在历史长河中又是短暂的。主人公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长,走过了平凡又不平凡的风雨人生,从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变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个人的成长经历也见证了共和国成长的风雨历程。以苏南农村一个生产队(现为村民小组)朱、张、夏三大姓三代人70年来的沧桑巨变为蓝本,借鉴苏南农村有关典型,创作一部反映具有历史厚重感的长篇小说,折射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人民共国成立70年来特别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我多年业余创作的一个梦想,现在这个梦想,终于可以开始实现了。虽然我已出版过16部文学著作,但这部著作无疑是我创作中分量最重的一部。所以在开始写下第一行字时,显得有些激动。正好,当天上午,太仓市作家协会、璜泾镇文联、璜泾粮管所举行了我的长篇纪实文学《听志愿军老兵施瑞林讲往事》的作品座谈会,在座谈会上,大家对我的这部著作作了精彩的评论,是对我创作的鼓励和鞭策,我也在会上讲到要在将近古稀之年,还应紧跟时代步伐,创作为人民抒怀为时代放歌的作品。
本书主人公朱建国是个正直、善良、聪明、勤奋的人,他总是为别人着想,与人为善,追求完美,但现实并不让他完美。难能可贵的是,他面对不完美的人生,没有失望,没有气馁,总是满腔热情地拥抱生活,在各个工作岗位上作出自己的不懈努力,书写出自己的精彩,也是同代人的精彩。他家三代人的命运,基本都是这样,都具有对党忠诚,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优秀品质,且下一代比上一代更趋完美,这是社会和时代的进步。朱建国退休后回到本村竞选村支书,虽然完全是虚构的,但在全国亦有先例,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不忘初心和对家乡这块土地的深情,以及迫切让家乡的父老乡亲早日过上好日子的美好愿望。同时,也是对未来振兴乡村的憧憬。本书还通过与朱建国一起长大的张忠良、夏永生三人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家庭变化,反映出新中国同龄人伴随着时代发展的成长经历和苏南农村普通家庭的渐进变化,证实了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跟共产党走,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才能越过越好的真理。
我在这部作品中塑造的人物都是普通人,最大的干部也只有副科级,最成功的企业也只有十来个工人的企业。因为我感到,只有从这些普通人身上发生的变化,才最能代表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实实在在的变化,他们身上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才能真正代表中国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才是我创作这部长篇小说的初衷。
我的这部作品力求具有鲜明的时代感和浓郁的地方特色,为了体现地方特色,融入了本地的乡风民俗和适度的方言。在文体探索中,尝试“无界文学”写作,运用小说的框架,散文的语言,纪实的手法。结构上每小节都能独立成篇,上下文串起来又符合逻辑关系。为了追求可读性,尽量做到主旋律与多样化并存,严肃性与趣味性相谐。
这部二十八万字的长篇小说完成于2021年7月1日,描写主人公的生活也截止到这一天。因此,也成为一部向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献礼的作品。
文末附录了文学评论家王迅先生为我的小说写的一篇评论,以期帮助读者更好地解读我的这部作品,在此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
第一稿:2020年12月31日于太仓阳光花苑
第二稿:2021年3月30日于上海东新苑
第三稿:2021年7月1日于太仓项门新村
四、评论
主流叙事的诗性建构——朱凤鸣小说略论
王迅
王迅 作为上世纪50年代初出生的作家,朱凤鸣有着与共和国共同成长的经历。尽管用代际来划分作家缺少学术含量,但有时候这样的划分还是会显示出它一定的有效性与合理性。朱凤鸣出生于1950年6月,距离共和国成立只有不到一年的功夫。共和国的成长充满动荡与曲折,世事烟云纷纭变幻,这构成了朱凤鸣小说创作的主要精神资源和写作背景。对于出生于这一时间“临界点”的作家而言,“理想”和“责任”仍然是这一代作家的关键词。某种意义上,在精神气质上所特有的一种道义担当与人文情怀,正是这一代作家与60后、70后、尤其是80后作家的根本区分。朱凤鸣是一个以素常情怀和严肃笔调写作的作家,他的作品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小说在题材上贴近现实生活,紧扣社会、政治与历史,具有浓郁的时代气息和地方民俗色彩;在美学品格上,传统与现代兼顾,朴实与厚重相容,给人以诸多现实的思考和人生的启示。在很大程度上,这些特点建构了作为一个主流作家所必备的文学气质。
但是,主流叙事并不就是我们常常所认为的那样:“道”大于“文”,思想大于形象,教育意义大于艺术意义。在朱凤鸣的小说中,作者所秉承的是,“道”与“文”相称,思想与形象相融,教育意义与艺术魅力并重的文学观。他的作品具有很强的思想性,但作品思想的表达却不是说教性的、概念化的,也不是时下那些新闻纪实式的“现实主义作品”,而是以一种如海登·怀特所说的“有意味”的形式传达出来的。
就小说艺术本体而言,小说的本质特征是虚构性,它是一门虚构的艺术,所以,小说留给作家的艺术表现空间是相当宽广的。作家可以根据叙事结构的需要任意地虚构人物,编造故事。在这方面,朱凤鸣可谓是深得其要领,他说“我可以根据小说结构的需要,将张三的事安排到李四头上,把王五的习惯变成赵六的行为”。[1] 无疑,小说艺术巨大的表现空间为作家开辟了文学表达的自由领地,开启了艺术创造的生机,但同时对作家的想象力也构成了巨大的挑战。没有想象就没有创造。作家只有插上想象的翅膀,才能在艺术的天空自由地驰骋与翱翔。诗人借助想象创造意境,小说家也需要通过想象营构一个虚构的世界。这对于写诗出身的朱凤鸣来说,应该不算难事。事实上也是如此,他的中短篇小说集《冬日的欲望》和长篇小说《小镇美女》等就显示了作家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和小说艺术虚构的魅力。
在商品化物质时代,商家纷纷推出各自的品牌以获取巨大的商业利润,“品牌效应”、“名人效应”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它深深地刻进了人们的记忆中。但是,这种商业化行为模式是否就是一条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金科玉律呢?对于文学写作而言是否也是如此?当我们读了朱凤鸣的中篇小说《制造名气》之后,或许会得到答案。小说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我”曾是一名部队复员回乡的民办小学教师,出于对文学写作的酷爱,“我”辞去了繁重的教学工作,意欲腾出更多时间来实现雄心勃勃的“三年创作计划”。辞职后,“我”带着憧憬不分昼夜地埋头写作,但收效甚微,不是寄出的稿子被退回,就是遭遇编辑精心策划的骗局,甚至妻子小孩也离开了自己。“我”后来发现报刊上发表的那些作品,其实并不比自己的好到哪里去,“只要有了名气,什么都好办”。于是决定:“我首先要办出名。”接着,小说以很大篇幅叙述了主人公通过各种手段制造名气。比如举办“退伍兵家庭图书馆”,毛主席像章纪念展,“向雷锋同志学习”图片纪念展等。主人公不免有些疯狂的行为不仅为他带来了“名气”,随着“名气”而来的是文章纷纷见诸报端,甚至为他赢得了爱情。但“名气”真的就那么靠得住吗?小说的悲剧性结尾昭示了那些投机取巧的人之可悲可叹。在表层上,作者以辛辣的笔触鞭挞了那些靠“名气”吃饭的所谓“作家”,反讽意味显见。但如果我们更进一层思考,朱凤鸣的叙事企图显然远不在此,他精心塑造的主人公是一个活生生的真实的生命,具有深厚的现实基础和艺术内涵。《制造名气》所开掘的主题显然是相当深刻的,因为它所真正要追问的是现代社会中商业化的行为,甚至是全球化的经济浪潮对人的影响,对人的生存的影响,其寓意是颇为深远的。
与《制造名气》一样,中篇小说《老支书》也是第一人称叙事,但这部小说在审美形态上似乎更具形式意味。小说的主人公老支书是叙述者“我”的父亲,是一位精明能干,一生为民的农村基层干部,因为他的实干精神和正直作为,父亲受到当地镇政府的重用,并一度升迁,到更大的乡镇担任重要职位,其业绩辉煌一时。但好人多磨难,老支书因为业绩显著坚持原则而遭人嫉妒暗算,退休后工资待遇大不如从前,甚至要被退出单位的公房。更为不幸的是,父亲被诊断为胰腺癌,胰腺癌在当时是不治之症。朴素的乡民在得知老支书身患绝症后,纷纷前去看望。但是,父亲的单位与医院近在咫尺,他却没有得到任何领导应有的关怀和慰问。最后,父亲单位的领导迫于上级领导的压力才赶到医院,虚情假意地慰问一番。从老支书凄凉的晚境中,读者会为老支书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而感到愤愤不平,同时也能看到导致这种不公正现象的深层社会原因。在艺术表现上,作者并没有把人物放在紧张激烈的矛盾冲突中进行刻画,从而塑造出一个高大的基层干部形象,也不是完全依凭好与坏、善与恶等简单的二元对立标准对人物评头论足,而是采用了“过去时”的回忆视角,由小说主人公的儿子,即叙述者“我”对父亲的一生进行重构与复现。叙述者视线的转移与挪动,强劲地推动着故事情节不断向前发展。在整个叙事中,作者与叙述者是分离的,作者并不参与对老支书及其故事的任何评价,因此,在叙事语调上,小说显得相当客观而真实。随着叙述者的叙述角度从充满稚气的童年视角到为父亲抱不平的成人视角的转换,读者可以不受作家的主观干扰而真实地感受到人物的生存现状,看到由叙述者所打开的老支书的人生世象以及人物性格的各个侧面。值得一提的是,叙述者回忆的视角、冷静的叙述语调在形式上形成一种沧桑感,在这种氛围中,老支书的一生显得更为悲凉也更为高尚。
朱凤鸣的小说叙事艺术的独特造诣还体现在,他的小说(特别是短篇)在叙事的末尾并不直接指明故事的结局,而是留下一个别有意味的“空白”,在绘画艺术上也称为“留白”。从接受美学上讲,这样的作品言有尽而意无穷,往往会给读者留下充分想象和主动创造的可能。从这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窥见作家深厚的美学功底和难得的艺术才情。就具体的文本来看,短篇小说《天真难容》不仅在叙述方式上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先锋文本,而且在艺术形式上也颇有它的独特之处。叙述者“我”是追索雪的传奇故事的局外人和探访者,试图进入雪与乔的世界,弄清真相并尽力挽救雪,但最终却不了了之。这或许暗示着我的救助行为就像小说中的女主人公雪一样,太天真,太不切实际,所以难以收到实效。雪的命运究竟怎样?她最后是否得救?小说诗性的结尾耐人寻味,给读者留下了很大的思索空间。在结尾的处理上,与《天真难容》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是短篇小说《老陈的儿子梦》。老陈在去书店的路上偶然碰到一个乞讨的男孩陈东,便高兴地将他带到家中,并打算收养这个孩子以实现他多年的儿子梦。但万万没想到的是,趁老陈一家夜间熟睡之际,陈东携带老陈女儿的手提电脑逃离老陈家。但公安人员很快抓获了包括陈东在内的三个乞讨的男孩,并通知老陈前去认领失物。出于怜悯之心,老陈不但没有怪罪于陈东,反而慷慨地拿出一千元作路费,让三个孩子回家过年。小说的最后,老陈收到陈东的来信,并看到陈东母亲在遗嘱中答应儿子让别人收养的消息。这是否又是一个骗局?或者说,对老陈来而言,收养儿子永远是一个无法实现的梦?确实,老陈的天真所为令人捧腹,也很可能难以见容于社会,但他的善良之心令人感动。小说的叙述在老陈的默默祈祷中嘎然而止,给读者留下无限遐想空间。至此,两篇小说在主题上不谋而合,真可谓“天真难容”!
作为江苏太仓市作家,朱凤鸣在创作中对养育自己的江南水乡“人间天堂”故里投入了相当的热情,几乎构成了他小说创作的原动力。尽管他尽力把笔触伸向历史的深处,将政治风云与经济浪潮打入叙事,极为真实地揭示了解放以来中国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因社会的变化而带来的人世沧桑。但是,他的小说并不直接对政治事件和经济现象进行描述,而是通过审美的方式间接地或艺术地传达出来的。在创作中,他通过审美加工,把质朴的乡风民俗变成活生生的文学创作素材,将人物描写与风俗画、风情画的刻绘融化在故事叙述之中,具体而深刻地反映了上世纪50年代直至当下苏南太仓一带的的乡村生活,使小说染上了十分浓郁的地方民族色彩。在他的小说文本中,这种审美特征最为典型地体现在长篇小说《小镇美女》的叙事中。虽然在主体上,小说主要叙写了太仓某小镇美丽的三姐妹颇具传奇色彩的曲折人生经历,但别具特色的民俗风情描写在相当程度上构成了《小镇美女》的美学底色。在叙事的推进中,融进了当地的生产劳动、饮食起居、婚丧嫁娶、宗教文化、民间文艺等各个方面的乡风民俗。如保根结婚一节,保根和一群人到金华家接亲,一伙熟悉金华家的人干脆从后门进去,金华的父亲见状便不放鞭炮,也不让接亲的人将嫁妆抬走。这一细节显示了小说叙述幽默的一面,更体现了作者对当地婚俗状况的观察入微。从小说很多类似的细节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对苏南太仓一带的民情风俗是相当熟悉的,这种生活积累反映在小说中,便是对风俗画、风情画的相当精微、细致而又十分到位的叙述。又如下面一段:
当地乡下人喝酒吃饭是很有规矩的,每桌上必有一个人先请吃哪一个菜,客人才能一起动筷子,已吃过的菜才能随便吃,如果有哪个人随便吃了哪个未开吃的菜,就要被人认为没有教养被人看不起,而一起赴宴的小孩往往不懂这些,看到自己喜欢吃的菜就要伸出筷子,常常要挨大人的责骂,甚至挨打。保林有几次忍不住,想把筷伸向未开吃的菜,不是被舅舅咳嗽止住,就是被保根瞪眼止住了。[2]
这段文字细致地叙述了当地别具风味的餐桌礼俗,透露出浓郁的乡间民俗民情的风韵。《小镇美女》正是在独具特色的乡俗民情的描写中,作者将鲜明的人物形象、生动曲折的故事与复杂的人世纷争和盘托出,折射出人在时代的浪潮中奋力挣扎、不断勘探新的人生道路的内在潜能和精神力量,同时,使整部小说的叙述带上了强烈的传奇色彩,从而增强了文本的可读性。
朱凤鸣的小说世界所展现的不是乌托邦式的桃源仙境,也非虚无缥缈的空中楼阁,而是弥漫着强烈的时代气息,洋溢着丰盈的生活质感。中短篇小说《老支书》、《局长与疯妻》、《老队长之死》、《月光曲里的咖啡柠檬》,甚至长篇小说《小镇美女》等大多数作品,都不约而同地把自己的审美眼光投向了中国的现实政治经济生活当中,诸多新的经济政策的发端、探索、开花、结果等在他的小说叙事中展露无遗,极为深刻地揭示了各个时期的时代风貌和本质特征。但是,对于时代气息的呈现与生命记忆的追索,朱凤鸣的小说不是采取新闻报道式的实笔记录,而是借鉴了中外小说的叙事艺术技巧,把现代叙事艺术与生动曲折的故事有机地融合在一起,讲究形式,突出叙述的诗性品格与形式功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
注释:
[1]朱凤鸣.热爱小说的理由.冬日的欲望[M].北方文艺出版社.2005.252
[2]朱凤鸣.小镇美女[M].北方文艺出版社.2006.67
(王迅,男,1976年生,湖北荆州人,文学硕士,文学杂志编辑,文学评论家,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曾于《文艺争鸣》、《民族文学研究》、《文艺报》等核心报刊发表论文数十篇。)
(编辑:moyuzhai)









